
《雪线上的奔布拉》连载(2)丨孔书记这个汉族人的眼神让我睡不着了
2024-12-27 09:17:00 发布 来源:大众报业·农村大众客户端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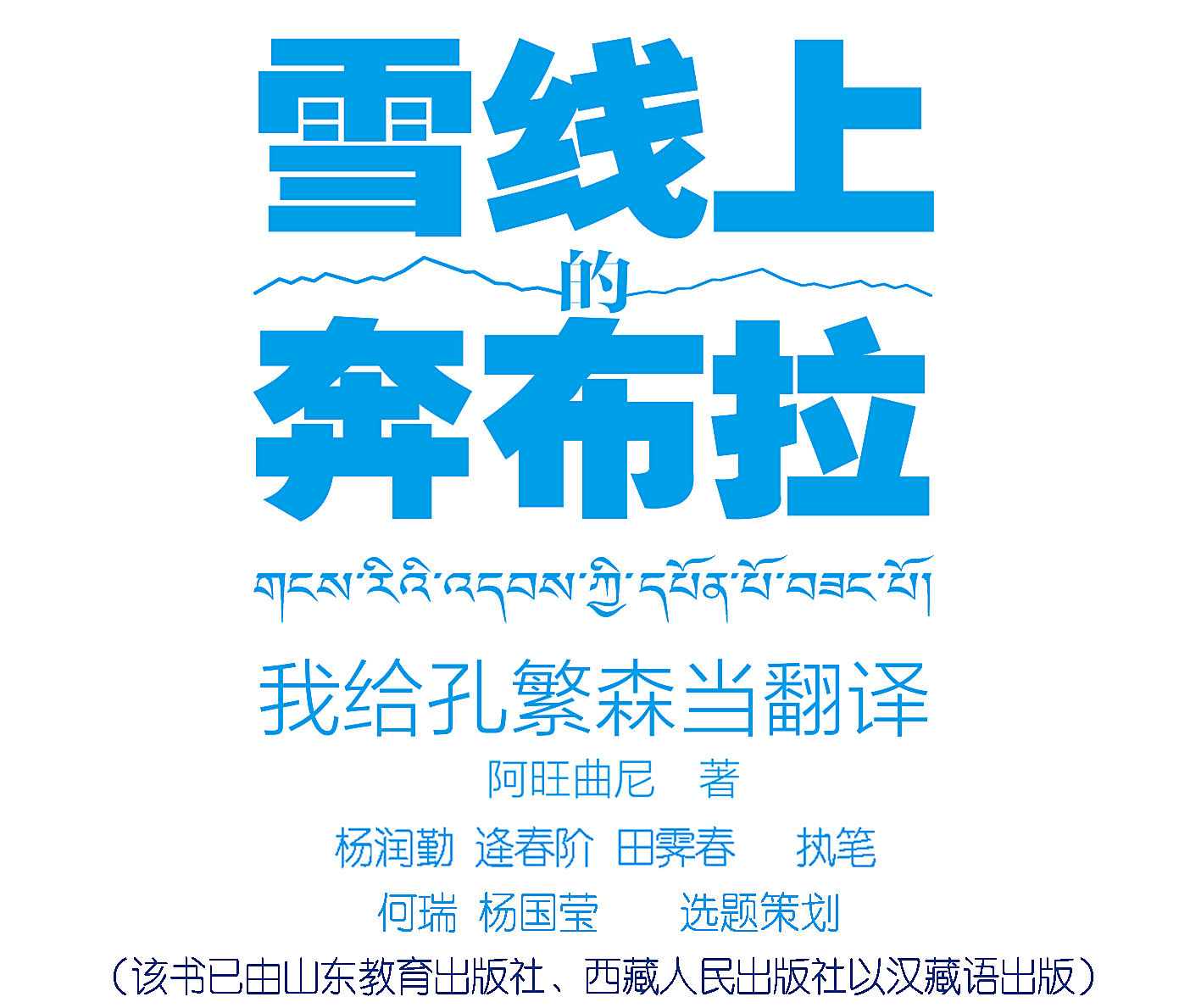
第一章 初识·那灼人的眼神
要让人信服就得有理由,这个理由就是干出实事,让老百姓受益。干出事之前,咱们就得当这个“傻瓜”。
2.他一口一口地吃着清水拌糌粑,脸上挂着青一块、紫一块的伤痕,因缺氧而青紫的嘴唇一张一合……
夜里没睡好,岗巴风大,我听了一夜的风声,其实不是风声,是孔书记这个汉族人的眼神让我睡不着了。那眼神是听了贫困的牧民生活后流露出来的,那眼神是急切,是焦灼,熬红的眼睛像烧红了的烙铁,一烙铁一烙铁,烧得我心疼。一个汉族人,对藏族人这么上心……后来我迷迷糊糊地睡去,等醒来时天已放亮,孔书记已经起来打扫院子。他跟我说,这是他当兵时的习惯,早睡早起,起来就抓紧整理内务。
我赶紧去马厩牵来一匹枣红马,我答应过要教孔书记骑马。
我先告诉他骑马要领,他一点就透。可是毕竟没骑过马,他刚一骑上去,那匹马嘶叫着旋转起来。我高喊着:“骑稳,孔书记!”他松松马缰,那马立即发疯般又踢又跳。顾上这顾不上那,急得他满头大汗,也紧张得我心悬在嗓子眼儿。没想到午饭时,他已经学会拨弄马鞭,骑马忽左忽右地顺路小跑了,下午就能骑着马到附近的村里转了。不巧,在一个转弯处遇见一群羊,牧羊人鞭子一响,马惊了一下,随即前蹄高扬,“咴咴”直叫。他重重摔下马来,半边脸上擦出了血。我一急,拿起马鞭照马抽打起来。
他爬起来,一把拉住我的手说:“不能怪它,是我骑人家,它可能是累了饿了想吃饭了。牵回去喂马,加点儿料,咱们明天出发去昌龙公社。”
我看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马脸,马儿长嘶一声,忽闪着一双明亮的大眼,抖鬃扬尾,像是听懂了他的话。我又看到了他那火炭般的眼神。
第二天早上,我们骑马去昌龙。看他翻身上马时吃力的样子,还有他那蜡黄疲惫的脸,我心里不忍,劝他再歇两天。他说:“再歇两天也是这样,高反根本算不了什么,它反它的,我干我的。”
我说:“你还不知道厉害。听说,有个内地干部,前几天进藏,感冒引起了肺水肿,还没到医院,就没了气。”
他说:“我命硬,没那么娇贵。”
我们的“行头”,是一人一个背包,背包里是铺盖、几件衣服和糌粑,他的背包里还多了一个柳木菜墩。另外,一人有一个黄帆布挎包,里面是水壶、手电、笔记本、火柴。他的笔记本是红色塑料皮的,32开,挺厚,太阳一照,折射着暖暖的红光。他还有一个深褐色的药箱,正中有一个红色的“ 十”字,肩上的黄挎包背带与药箱的背带在胸前交叉,像极了部队行军途中的一名卫生员。
他腰间还别着一把五四手枪,我肩上背着一支半自动步枪。岗巴在边境线上,那时还有敌情。
骑在马上,大好风景扑面而来。岗巴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,有“天边岗巴”之称。从岗巴往西南看,喜马拉雅山山体呈巨型金字塔状,珠穆朗玛峰拔地通天,气势磅礴。岗巴的正南面是确姆约钦雪山和康钦甲布雪山,所以岗巴在藏语里意为“雪山附近的村庄”。
美景是美景,但这里大多数牧民还在为温饱发愁呢。
糌粑是岗巴人的主食,将青稞洗净、晾干、炒熟后磨成面粉,食用时加入酥油茶、奶渣等,用手捏成团吃。可青稞是种出来的,吃饭,要看老天的脸色,老天一变脸,可能就颗粒无收。对岗巴人而言,糌粑不是在手里握着,而是眼前飘着、晃着,逮着就吃,逮不着就饿着……
岗巴长冬无夏,春秋相连,人们在稀薄的空气和寒冷的气候里生活着,就像进行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。岗巴在大天大山之下,像一个历经苦难、想长也长不高个子的孩子,它哭着、闹着,寻找着心中的菩萨。
岗巴的“地画”是一个个博巴(藏族人的自称)的脸,深深的皱纹里流淌着汗水和泪水。挥掉泪水,祈圣灵五体投地;挥掉泪水,让歌声响彻云霄。让日子一天天好起来,好起来吧——扎西德勒(藏语,意为吉祥如意)。
从古至今,藏族人千万遍地说着,喊着,祈祷着——扎西德勒!扎西德勒!扎西德勒!声音那么坚定而又执着。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。
从岗巴县城到昌龙60里,山路时陡时缓,曲里拐弯,走过这架山再翻那道梁。日头偏西,来到一条河边。我说,咱下马在河边歇会儿,再走十几里就到昌龙了。他下了马吃力地岔开两腿走,我知道这是刚学会骑马把大腿根磨肿了, 就搬块石头让他坐下。
虽是5月,河边还有冰碴子。河是雪山的融水,清清亮亮。孔书记用手捧水喝了一口,抹一把嘴,连说好水、好喝,随即从背包里拿出糌粑倒在铝饭盒里,从河里撩点儿水用筷子搅拌着。我说:“我们藏族人不用筷子,用手指头捏糌粑。”他说:“入乡随俗,捏。”没有热酥油茶糌粑捏不拢,他就使劲地捏,捏来捏去还是散,末了干脆把糌粑渣倒在手心里,一下子捂到嘴里。

岗巴县城至昌龙的路上,结着冰碴子的河水。(杨国莹 摄)
孔书记嚼着,又问藏族人还有什么讲究?我说讲究多了,如果有人敬你青稞酒,你不能端起碗就喝,要用右手的无名指轻轻蘸着弹三下,一敬天,二敬地,三敬对方,然后才能喝;献哈达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尊重;进门时不可以踩门槛;到藏族人家入座可盘腿而坐,不可将脚伸直,脚底向人,等等。
他再问,这里农牧民的穿戴有什么说法?我说,岗巴的男人穿带袖的氆氇呢藏袍,戴传统的金丝帽,有的还腰佩藏刀,夏天戴毡帽,冬天戴皮帽。头发用彩丝线配在一起编成长辫盘在头顶,腰系红毛线编成的长腰带,耳朵上戴耳环。妇女穿无袖氆氇呢藏袍,头发用红、绿等颜色的丝线配在一起编成长辫盘在头顶……
没想到,孔书记竟然拿出那个红皮笔记本,认真地记着。
他一口一口地吃着清水拌糌粑,脸上挂着青一块、紫一块的伤痕,因缺氧而青紫的嘴唇一张一合……如果不是亲眼所见,我真的不相信,这是一个山东来的大奔布拉。
骑马再行几十里,山路颠得屁股疼,颠得他直咧嘴。眼前是一个宽阔的牧场,一大群羊正在吃草,一只棕红色的藏獒看到我们发出低沉而洪亮的叫声,一位白须飘胸的老人骑在马上喝住了它。
我下马向老人双手合十,用藏语与他交流,得知他是普村人,叫巴旺,已经80多岁了。他放了一辈子羊。今年天旱,牧场里的草长得不好,再过些日子他要赶着羊群进山放牧。
孔书记让我问他这里农牧民的生活情况。巴旺老人说,村里 100多口人,600多亩地,青稞收成看天,年年都不够吃,每年藏历年村里人才能吃上队里杀羊分的一点儿羊肉。家里劳力少、孩子多的就更苦了,饿肚子,没衣穿。
我翻译给孔书记,他在笔记本上记。
老人问我们是来巡逻的(我背上有枪)还是来看景的,我说是和山东来的援藏干部一块在昌龙蹲点。他又问,什么是援藏?什么是蹲点?我说,援藏就是支援西藏,蹲点就是来昌龙工作。
老人听后仔细打量着我们哈哈大笑起来,白胡子翘得老高。孔书记问他为什么笑,我翻译给巴旺老人。
老人说,他以为援藏和蹲点是带来了多少头牛,多少只羊,多少钱财。你们来两个人能管什么用?一个细皮嫩肉,一个瘦得像干树枝,一场风暴就把你们刮回去了。
我翻译给孔书记听,他先是皱皱眉头,接着又面带笑容向老人双手合十说:“老人家,我们没带什么钱财,我们来就是和藏族同胞商量着干事的。”
老人轻蔑地一笑:“‘聪明人用成果说话,傻瓜才用舌头吹牛’,这是我们藏族人的谚语,你们琢磨去吧。”
“我们不是吹牛!老人家。”
“我见的人、经的事儿多了去了。走吧,走吧。别费嘴了。”
“老人家……”
老人家使劲甩一下手中的鞭子,“唉——”,长叹了一声。
走出牧场,孔书记表情尴尬,他低着头想了半天,忽然回头像是自言自语,又像是对我说:“要让人信服就得有理由,这个理由就是干出实事,让老百姓受益。干出事之前,咱们就得当这个‘傻瓜’。”
天近傍晚,我们走进了公社大院。最先见到的是昌龙公社党支部书记格热。他身材魁梧,说起话来声如洪钟。他道一声贡卡姆桑(你好),笑呵呵地把一条有些泛黄的哈达戴在孔书记脖子上,双手合十,嘴里连说着扎西德勒。格热从当地驻军那里学过汉语,我这个翻译成了听众。
孔书记打开笔记本,让格热介绍每个村的情况。格热把乃村、林嘎村、纳加村、普村、雪布让村、铁布公村、亚欧村的人口、耕地面积、牲畜存栏情况说了个遍。

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村庄。
当提及农牧民的生活状况时,格热低下了头。
昌龙距喜马拉雅山更近一些,藏语的意思为“冷沟”,其实,这个“沟”是相对喜马拉雅山而言,这里海拔最高5788米,是“生命禁区的禁区”,主要山脉有曲登尼玛、孜拉岗日、朗木珠等,寒冷干燥,雨水稀少。全公社半农半牧,因这里土地含沙量高、保水保肥能力差,世世代代缺水的昌龙,最害怕的是干旱,轻则减产,重则绝产,许多农牧民连肚子都填不饱。有的人家实在饿极了,竟然宰杀了肚子里还有未出生羊羔的母羊……
“我是支书,我没干好,没能让大家吃饱穿暖,罪过!罪过!”
“格热书记,好日子不是一个人带来的,咱们一起想法子。”
西藏人性格豁达开朗,格热听后弯腰伸了伸舌头,大笑起来:“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。”
我怕孔书记不明白,告诉他,这个弯腰伸舌,表示对你的尊敬和崇拜。孔书记也笑着拱手说,要让所有的村干部心里都亮堂起来,咱们当干部的要天天想着怎么让群众过得好,要向群众伸舌头。
那天,在村办公室里,我们一直聊到夜里10点多钟。突然,格热一拍大腿:“走,到我家吃饭去。”
不由分说,一手拉着一个,一路上不撒手。
昌龙公社驻地是乃村,格热是乃村人,出了公社大院不远就是他家。进家门时,孔书记的头被门框撞了一下。格热说,藏族人家的入户门大部分都低矮,一来可以防风沙入侵,二来家家都有一间人神共居的经堂,或是一个佛龛,再穷的人家也有一张佛像唐卡。我们作为凡人每日出出进进,弯腰低首表示对菩萨的敬畏。另外,还可以拒鬼魅进屋,传说中妖魔鬼怪在夜间走路是横冲直撞的,且不会弯腰与拐弯,这样的门户可起到保家人平安的作用。

2000 年的安居新房。
格热家的陈设简单,一张桌子几个柜,几个小凳,墙上贴着毛主席像,旁边还有一张佛像唐卡。桌上摆了牛肉干、奶渣和干果。藏族人待客热情是出了名的,无论穷富,都要拿出最好的吃食招待客人,格热显然是把我们当成最尊贵的客人。
格热有四个孩子,两男两女,大的十四五岁,小的有六七岁。见我们来了,孩子们缩到了墙角,怯生生地看着我们。
格热的妻子拉吉倒上热腾腾的酥油茶,双手端给我们,淡黄色的酥油茶奶香四溢。孔书记则端着酥油茶走向墙角的孩子,格热拉住他说:“孩子们喝过了。”回头给孩子们使了一个眼色:“到羊圈去玩吧。”
格热又把青稞酒倒入碗里,自己先端起来,用右手的无名指“ 一蘸三弹”后说:“‘如果心是近的,再遥远的路也是短的’,宫珠得勒(晚上好),敬孔书记。”孔书记也学着格热的样子“一蘸三弹”,然后喝了一口:“祝愿好日子早些到来,扎西德勒。”
用炒面、酥油茶、奶渣和糖捏出的糌粑入口软嫩,又香又甜。孔书记连连说好,这是最好吃的西藏味道。接着,我们由糌粑的原料炒面、奶渣,聊到了农牧业生产,由农牧业又聊到农牧民的生活,直到午夜时分。
藏族家庭一般在屋内沿墙摆上矮矮的木床,能坐能躺能睡,床覆盖着卡垫(小型藏毯)。我们被让到里屋的矮床上睡,格热夫妇在外间打了地铺。孔书记不同意,格热拉着妻子往地铺上一躺,被子蒙头装打呼噜。我们无奈。正要睡, 孔书记忽然想起什么,急问我,四个孩子哪里去了。我心里咯噔一下,刚来时格热让孩子们去羊圈玩,不会是让他们在那里睡吧?
我们急急出门,来到院外的羊圈。我打开手电,见几十只羊卧在地上安睡,一只羊的肚子底下露出了孩子的脚。我翻墙进圈,见四个孩子有的抱着羊腿,有的贴着羊肚子酣睡。生人进圈,羊乱叫乱跑,羊蹄子把格热扎着辫子的小女儿踩得大哭起来。
孔书记脸色大变:“胡闹,这个格热!”
格热夫妇也来了。格热哈哈一笑:“不要紧,孩子们火力大,羊圈也暖和。”孔书记绷着脸道:“你真糊涂呀。如果让他们睡羊圈,我俩就到大街上去睡,再不登你家门。”
那晚,格热的四个孩子睡在了里屋的矮床上,我和孔书记在床边地上铺了草垫睡。睡前,他倒了半盆水,又从挎包里拿出条新毛巾浸了水,给孩子们擦了脸又擦了手,擦了小的再擦大的,边擦边问冷不冷,俨然像个慈父安慰受了委屈的孩子。擦着,问着,我看他眼圈红了。
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醒来,孔书记还是翻来覆去睡不着,我以为是高反,让他闭目深呼吸。

孔繁森、孩子们和羊群。
他说:“阿旺啊,想起刚才的事我睡不着呀。”
“在西藏这是常事,你是最尊贵的客人,理应受到这个待遇。”
“我不是客人啊。”
我心里嘟囔,您不是客人是什么,还不是过个一年半载,拍拍屁股走人?我们的日子还不是该咋过就咋过。我不能把心窝子里的话全都掏出来,毕竟,人家是大领导啊。于是,我顺着他说,不是客人,那就是一家人,可你是远道而来的呀。
孔书记说:“我来西藏前,搜罗了各种信息,还走访了几个‘ 老西藏’,他们跟我说了不少。我知道西藏跟内地比有差距,但没想到差距会这么大。”

岗巴县第一条公路——曲岗公路。
时间过去了30多年,站在孔书记工作过的街道上,我常常发呆。仿佛在梦中,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今非昔比,吃穿不愁,看病不愁,孩子上学不愁,牧民的腰包也鼓了。好多家庭都有了小汽车。更让人惊讶的是,我们的人均预期寿命由解放初的35.5岁提升到72.5岁,这是过去不可想象的。我感触最深的是交通,过去从日喀则到岗巴骑马得走一天,要遇到雪天,那就没准了。现在一踩油门,两个小时就到了。
点击查看《雪线上的奔布拉》连载已发内容









